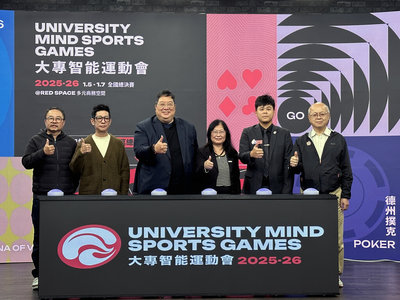吳念真:守護一個連結著記憶的語言
他說從未想過台語會消失,也不認為自己能作些什麼,但其實他已經走在路上很久很久
文:王思捷
有關吳念真自己的故事,幾乎都要由少年時代那段從車站走回家的上坡路,以及侯硐大粗坑的老家開始說起。有時不免驚訝,這個「台灣最有溫度的歐吉桑」下半輩子的記憶和養分,都從那段崎嶇不平的泥土路上和貧困的村子裡孕育出來。愛說故事的個性、說故事的能力和往後半世紀溫暖台灣千百萬人的力量,巧妙的濃縮在台灣東北角礦區長大的那個小孩子身上。
如果那些記憶是一部影片,配音自然是由台語構成的,而且就這樣原封不動的留在吳念真腦海裡。如果把媽媽的教誨、爸爸的斥責、同伴的訕笑聲全配上華語,那就像吳念真所說,《戀戀風塵》一度為了在無線電視台播映,而被迫將配音全改為國語一樣的荒謬可笑。
吳念真曾經給我們的感動,無論是電影《多桑》、舞台劇《人間條件》《再會吧 北投!》,還是保力達B廣告的旁白,絕大多數都使用台語。語言,或說台語,對寫作起家的吳念真有著什麼樣的意義,是「文化+」好奇的,所以在那個今年頭一次感到寒意的早上,有了這段訪談。
說起選舉...是件複雜的事
其實那不太像是場訪問,而像是看了場免費的舞台劇,66歲的吳念真或坐或站,一度跑了起來,幽默的對話則是必然。大家不停笑著,有時連攝影同事也忍俊不住,不得不暫時放下相機。
似乎難以避免的,對話以前陣子選舉和他罕見的臉書直播開場。吳念真說,其實他對政治人物的上上下下沒有太強烈感覺,倒是公投結果令他「傷心欲絕」,了解到原來台灣社會「蒼老保守到這個程度」,突然覺得自己不太了解台灣。
「不過也好啦,讓年輕人知道原來這世界不是他們想像的那樣」,他安慰著一大群為公投結果傻眼的年輕人,也像是在安慰自己。
然後他又比手畫腳的說起,投票前是如何試圖扭轉老婆對同婚公投的態度,老婆是怎麼樣無法理解公投題目「否定的否定」,投票日又差點被不作功課,在投票圈選處不知所措、扭捏十幾分鐘的選民氣死。
至於直播,純粹是因為對台灣每到選舉就撕裂、貼標籤感到無奈,直播是最快的溝通方式。「(選前)一直被罵,被罵久了也要發洩一下...台灣這麼小的地方,一起合作些什麼東西都來不及了,怎麼會只想著彼此撕裂...」
沒想過台語會消失
有關於台語,吳念真說他從未想過台語「需要保護」,但是也觀察到了「雖然講台語的人很多,台語卻慢慢在消失」的現象。他認為主要原因在於教育主體使用華語,相對於華語成為「主體語言」,台語已經成為我們的「附屬語言」。
「如果不是主體語言,生命力會減弱,(最後)一定會死,語彙會慢慢消失。」
我提醒他,「台語文進行式」先前訪問他的好友紙風車劇團執行長李永豐,李永豐也是這麼說的──會憂心,會想要發揚它,但台語「要真沒了,就是沒了啊」。基本上,吳念真是大概能夠同意這種說法的。
他說,保護語言是個「大題目」,他從來沒有想過、也不認為自己能夠作出多麼巨大的貢獻,「每個人在你的位置上不要讓這語言死掉就好」,政府也不要禁絕某種語言的使用,盡量讓它有表達和使用的機會。不過他也強調,千萬不要讓語言變成意識形態,否則「排擠就來了」。
舉例來說,選舉場合經常有人堅持使用台語,問題是有不少年輕人聽不懂,當你怪罪年輕人聽不懂、不會用時,等於強調出語言的工具性,成為一種區分你我的「識別符碼」,這時候排他性就出現,對語言發展並非好事。
他說,之所以習慣在自己的戲劇作品上使用台語,並不是出於意識形態,而是因為那就是他筆下的人物和年代所使用的語言,是求真,是重現當時的場景和情境。「4、50年代的兩個鄉間農人,一定是說台語而不是國語...創作是為了表達某個年代的東西,我從未想過台語會消失,但是我們能力無法改變它,你只能盡量使用它」,他這麼說。
媽媽傳下來的語言
吳念真再度說起一段經常提起的兒時記憶,有一次母親和父親吵架,媽媽說:「我一世人拿三支香,從來毋捌講過家己的名」。他說,這並不容易在第一時間聽懂,媽媽的意思是她終其一生拿香拜神,都是求老公、兒子或家庭的好,從來不曾想過自己。
「但這種話用國語來講,就有點噁心,」他說,台語腔調和字彙有它獨到的一種美麗,有些東西就是用台語來表達才精準有味道。
「母語」之所以為母語,真不是叫假的,吳導的另外一個例子還是和媽媽有關。
他說,初中時從學校搭車回家後,還得走一個多小時的上坡路回家。當時媽媽就在半山腰的一家礦廠作挑礦石的粗工,有一天他走到工廠突然發現媽媽還沒下班,母親說她必須加班,要吳念真趕快回家煮飯給弟弟妹妹吃。
「天色黑了,我跟在媽媽背後,看著她雙肩挑著很重很重的石塊,在夜色中氣喘吁吁的慢步走著。你知道我這個人從小情感就很脆弱,看著她的背影就哭了。此時媽媽轉過身來說了一句話:『哭啥?咱夠卡辛苦嘛愛笑乎天公伯仔看!』」
幾十年了,這句話他一直記著;記著的原因,不只是因為那是媽媽說的話,也因為裡面傳達出很不一樣的人生哲理──「老天讓我們這麼辛苦,我們就愈要嘻皮笑臉的面對它,嘿嘿嘿的對著他笑,氣死它」。吳念真在描述這段時,真的對著天空扮起了鬼臉,表情還是像個十幾歲的少年一般促狹。
(本文節錄自中央社「文化+」雙週報第26期「2018台灣文化+視角」,12/24出刊)
本網站之文字、圖片及影音,非經授權,不得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及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