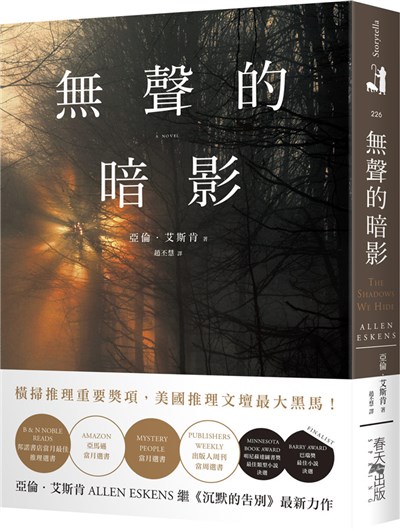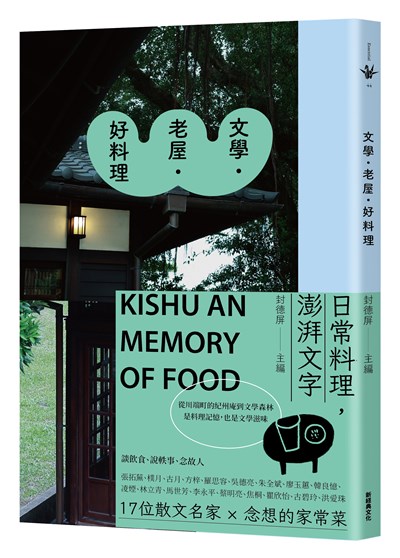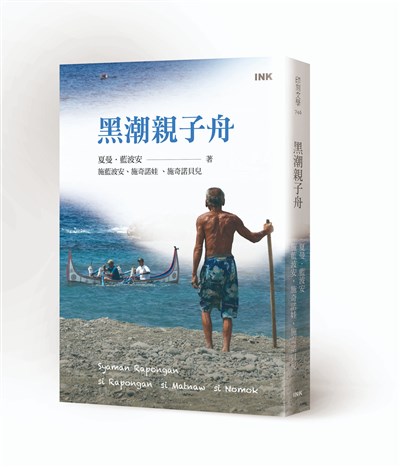2015開卷好書獎‧年度好書‧中文創作
推薦理由:除了淵博的知識、豐富的閱歷為讀者所熟知,詹宏志還是個說故事的高手,總能以別具一格的視角或觀點,在枯燥平凡中找到有趣,在有趣中找到深刻的意涵。跟著他去上山下海去旅行,或鍥而不捨地追求種種美食的奇遇,一定十分好玩。如果做不到,看他的書也很過癮。(羅智成)
——轉載自《中國時報‧開卷》
文章節錄
《旅行與讀書》
旅行的意義
好像是一種害怕「落伍」的心情,當我編選完自己關於「旅行」文章的選集之後,第一個「求助的」對象正是我那位為創業栖栖楻楻的兒子…。
因為前幾年出版的兩本文集,每當有朋友熱心回應:「這書寫得太好了,我讀了充滿共鳴…。」我冷靜打量著他(或她),這位「有共鳴」的朋友通常已經年過五旬了。這彷彿也是人生真相,年輕的時候我寫各種廣告文案,總是信心滿滿,覺得自己能夠找到合適的話題與言談方式,打動各色年輕人;然而有一天,我突然間覺得坐立難安,發現「那個能力」消失了,我對年輕人的心情與感受似乎失去了接收的天線,訊號顯得駁雜不清;而從我自己口中說出來的某些話題與用語,也開始變成「推開」年輕人的「老人符號」,他們的反應變得客氣拘謹,也有點避之唯恐不及的疏遠…。
為了不要讓自己的書變成「老人讀物」,我覺得需要一些「年輕人」的意見,但同學、同事和朋友都已經開始退休養生、含飴弄孫,我去那裡找可以諮商的年輕人呢?只好敲敲隔壁房間二十八歲偶而回來的「室友」,拜託他抽空看看我的稿子。略帶「文青」氣息的兒子花了幾天看了稿子,推推眼鏡,沈吟半晌,很客氣地說:「嗯,我看起來是還好啦…。」
問他有沒有什麼意見,他倒是毫不遲疑:「太雜了,你什麼都捨不得丟,很多文章性質不同,卻都放在一起,讀起來感覺很不一致。」這個切中要害的批評我倒是瞎子吃湯圓,心裡有數,但不是我真正的擔心與關心,我只好更直接地問:「你覺得年輕人會不會看這樣的書?」坐在我面前這位可能「不具代表性」的年輕人變得面有難色,支吾地說:「嗯,很難講,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說很遙遠,文章又那麼長…。」
唉,在寫這些文章的時候,或者說在我寫過的每一篇文章,我心中想的閱聽對象也確實一直都是同一位「年輕人」,只是這位熟悉的年輕人如今青春不再,與我偕老,而新的年輕人如今都是陌生人了;我那些自以為「循循善誘」的言談方式,如今在「臉書」快速回應的時代裡已經變得「太長了」(也太老了)…。
但我還是聽從這位現代文青的忠告,回到筆電「桌面」,狠狠刪去三分之一的稿子(但怎麼辦?還是剩下二十萬字,當然是「太長了」),基本上,所有「夾議夾敘」的論述文章都拿掉了,只留下「夾敘夾議」的說故事文章為主;最後,所有帶著「旅行論述」意味的文字都放棄(只剩一篇附錄),這就變成了一本像是以「旅行敘述」(travel narrative)為主調的「遊記」。
我倒開始感到汗顏,我自己的旅行遊蹤有什麼可以記錄之處?這裡並沒有什麼艱難辛苦的路線與地點,也沒有什麼驚異駭人的情境與遭遇,更沒有千鈞一髮的危險與轉折;若要說這些旅行有什麼獨特,也許只有一點點散漫隨興的旅程,加上一點點「與書相遇」的個人風格…。
散漫隨興,是因為害怕有固定節目的集體行程,特別是那種節目滿檔、喧嘩慌亂的行程;事實上我對所有既定觀光行程與特定地標都有恐懼,總覺得人生片段變成了某種鑄模澆灌。旅行裡讓我留下深刻印記的經驗往往發生在最無目的的時候與場所,樹下小酒店的一杯沁涼白酒,迷路崎嶇城區偶遇的小麵包店,異國鄉間等待公車窺見的鄉民日常生活景致,這些無意間得來的吉光片羽反倒成了日後反覆咀嚼的旅行滋味。
與書相遇,說的則是自己的旅行來歷。是什麼決定了一個人旅行的目的地?又如何決定那條從這裡到那裡的旅行路線?在我的例子裡,很少是因為身邊朋友的推薦或描述,大部分是來自各種因緣際會的閱讀經驗;也說不上來是什麼樣的閱讀,有時候就是闗於當地的敘述(譬如峇里島),有時候來自小說家的描繪(譬如傑克.倫敦筆下的阿拉斯加),有時候就來自於探險家或文學家腳蹤,譬如說會來到非洲贊比亞(Zambia)的維多利亞大瀑布,自然是因為傳教士探險家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的緣故,但坐在瀑布辛巴威這一側「維多利亞瀑布旅館」的酒吧裡,點一杯叫做「我推測」(I presume)的雞尾酒,心裡感到激動與滿足,覺得歷史與自己相會,那就是十足的書呆子氣味…。在探險文獻裡,當新聞記者兼探險家亨利.莫頓.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應召深入非洲尋找下落不明的李文斯頓,結果他穿行叢林七百哩,真的在今日坦尚尼亞的鳥濟濟(Ujiji)找到李文斯頓,傳說中,他在部落民層層圍觀之下走向那位略顯虛弱的白人,拘謹地說:「是李文斯頓醫師嗎?我斗膽推想…。」(Dr. Livingstone, I presume?)這是旅行與探險史上一個令人難忘的場面與對白,書呆子不可能不對這杯雞尾酒感到激動。
是的,「為書所成,為書所毀」(made by books and ruined by books)真是我的人生寫照,即使在行走途中也不可免;對我來說,帶著1920年版的倫敦「藍色導遊」(Blue Guide)遠比帶著2014年的Lonely Planet指南有趣得多,雖然毫不實用(我真的幹過這種事);但旅行的真義之一不過就是「想像他者的生活」,我多麼希望走出倫敦旅館門口,伸手招到的「兩人座小馬車」,而不是黑頭計程車,那才是我錯過的、無從複製的人生,除非威爾斯(H. G. Wells, 1866-1946)的「時間機器」(time machine)再現江湖,否則我們是不可能旅行於時間軸的另一段時光…。旅行,因而只能是空間的移動,無法是時間的逆旅。
只有一個人生是令人不滿足的,但我們誕生之際時空已定,這個人生也就跟著「註定」,我們還有什麼方式能讓我們擴大實體世界與抽象世界的參與,在我看起來,也許只有「旅行」與「讀書」能讓我們擁有超過一個「人生」。讀書時,你固然要融入情景,因而有了另種人生的感受;旅行時,我們也要想盡辦法糾纏地,假裝另一種文化與生活的短暫化身,這也是我不愛「旅行計劃」,也不喜歡「安全旅行」的緣故,如果我們沒有大膽一點,我們永遠只是戴著「家鄉之殼」去旅行的人,沒有接觸異世界,也就沒有短暫的另一個人生…。
這不是一本有參考用處的旅行書,一切實用資訊全部付諸闕如,你不能照抄其中的路線去旅行;這也不是一本有文學企圖的書,沒有含蓄節制和優美辭藻,他像是一個喋喋不休的返鄉浪子,體能已衰卻談興頗高,他興致勃勃對著那位未滿二十的年輕自己敘述自己窺探他種人生的各色經歷,至於那位年輕人是否有興趣傾聽,卻也不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