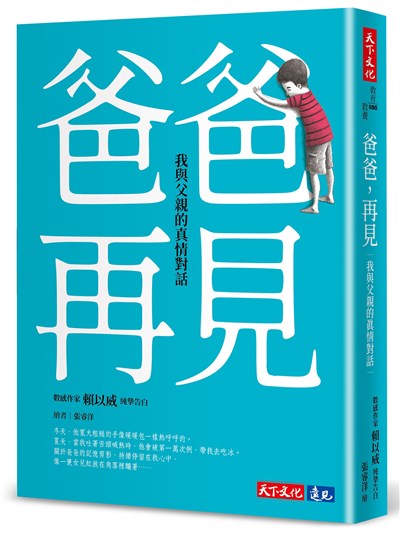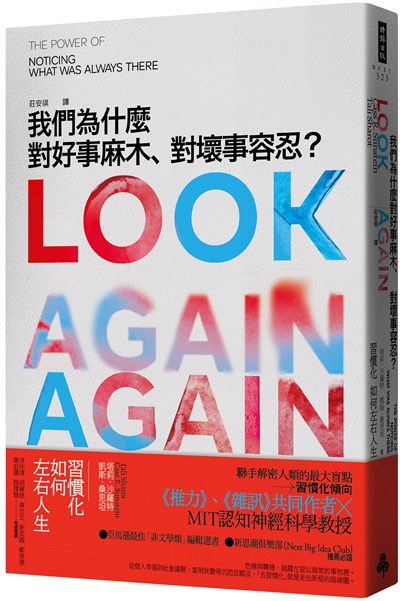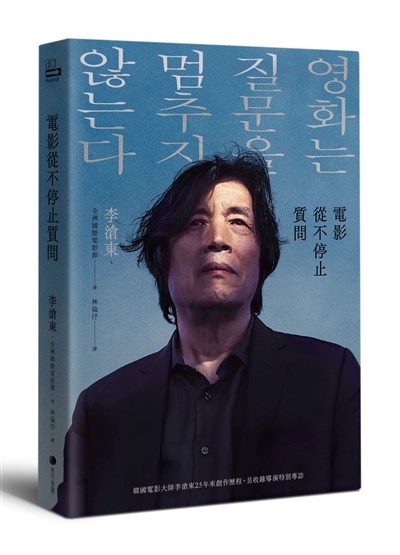
最會寫劇本的導演,最會拍電影的小説家?李滄東導演25年的創作人生
從1997年的處女作《青魚》到2018年《燃燒烈愛》,李滄東的電影一貫被投以「美麗」、「文學性」,乃至於「傑作」的讚賞,無一例外地受到了全世界觀眾和評論界的關注。
其實,早在初期作品登上大銀幕之後,李滄東便獲得了「現實主義大師」稱讚。李滄東導演將無法輕易解決或回答的問題的碎片融入電影之中,因此他的電影在上映後即便過了很長一段時間,重新觀影時仍會有新的感觸。
而我們,可以藉由這本《電影從不停止質問》,從電影評論與專訪中,窺探李滄東作為電影人的一生,從中了解他的工作世界,以及他對於電影的追求。
內容節錄
《電影從不停止質問:韓國電影大師李滄東,25年來創作歷程,另收錄導演特別專訪》
引言 看不見的世界的真相/尚—馮索瓦.侯哲 (Jean-François Rauger)
李滄東的電影之所以有強烈的文學層面,首先在於他的電影橫越了既有的電影類別,讓影評人寫出「李滄東是在執導電視劇」,或「他的電影中有喜劇元素」——而這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沒有考慮到戲劇和荒誕、可悲及平庸之間獨特的結合是他作品的特性。其次,是在於他的電影展現出決定韓國當代史和韓國社會的因素,與他電影中人物個性的不可分割性。
小說和歷史之間一貫的複雜關係,無疑在他的第二部電影《薄荷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這部電影甚至還成為一些理論實驗的主題。除了藉由一連串時間倒流的段落講述主角英浩的故事,李滄東似乎還意圖尋找一個也許無法到達的根源,也就是尋找(如同艾伯托.莫拉維亞〔Alberto Moravia〕1的解釋)揭露一個人作為「從眾者」的真相來源。英浩因著自己的選擇,自一九七○年代末起,光州屠殺事件到民主化之後的幻滅期這二十年間,也就是從鎮壓的時代(此時他是拷問警察)開始,到爆發外匯危機之前的過度繁榮期(這時他是生意人),根據社會及其變化,進行自我轉型。
沒有消失的罪惡感
然而深入探討《薄荷糖》潛在的因果關係,無疑是一種對原罪的探尋。這恐怕是對在包容不人道的情況下產生的愧疚的探尋,而這種罪疚廣泛來說包含向法律妥協,再更廣泛地說,是向很少有人尊重的「基本的做人道理2」這個簡單規則妥協後所形成。李的電影中充滿了罪疚。
《青魚》描述一個年輕人為尋找自身所缺失的共同體而進入幫派的旅程。他寧願選擇犯罪,也不願享受破裂家庭的虛假溫暖;《綠洲》講述的是一對奇妙情侶——年輕的男人像個孩子,而年輕的女人患有腦性麻痺。這對情侶的組成,可能是由一連串充滿謊言的事件所製造出來的結果(男人代替自己的親兄坐牢,女人的哥哥以她的名義非法取得身心障礙者住宅)。這難道不是金錢會污染並毒害人際關係的最佳寫照?在《生命之詩》,當男學生的父母為了壓下孩子們性侵少女所導致的自殺事件,給少女的母親慰問金時,讓人直覺聯想到罪惡感所具有的交換價值。以及在《密陽》中,幼子慘遭殺害的母親聽到犯人說自己已透過神諭得到原諒,這時讓她頓悟的,難道不就是信仰是一種忍受悲傷和缺席最實用的方法,而且還是一種即使犯罪也能活下去既便利又能消除罪惡的自私方法嗎?
沒有家人的人物
李滄東電影裡的人物都在追求他們身分認同感中必要的依戀、接納、共同體和家人,但他們每次都不被允許擁有這個條件,或因此處於困境之中,而這或許是因為引起這種慾望的焦慮和神經質的源頭就在於他們的家庭本身。這些家庭往往支離破碎、分散各地,無法好好發揮其功能。比如《生命之詩》的少年在父母離婚後,和外婆美子一起生活,與住釜山的母親分隔兩地;比如《密陽》的女主角先後失去了丈夫和愛子,她曾相信自己已經在其依託的基督教共同體中找到了安身之處,但之後她領悟到自己被他們滿口的仁義道德所騙,是受害者。又比如在《青魚》,一個剛退伍的年輕人試圖在幫派殘酷的兄弟情中尋找自己匱乏的基本連帶感。以及《綠洲》的主角,儘管他代替兄長自首,攬下車禍肇事致死的責任,並守住了家庭的名聲,最終還是被家人拋棄。最後,比如《燃燒烈愛》的主角發現社會階級的模糊。
李滄東電影的主角們迷失在一個被困於「利己主義的冰水3」的社會中心,他們似乎只擁有最原始的純真,或是對(從喬治.歐威爾的意義來說)人類「基本的做人道理」具有與生俱來的直覺。這一點被刻畫成《生命之詩》的老太太美子,以及《密陽》中由優秀的演員宋康昊所飾演,努力卻笨拙的戀人宗燦。
李滄東的人物在道德方面明顯單純(時而接近愚蠢),這不僅讓他們和唯利是圖的人產生區分,也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方式,讓他們觀察,仔細地深入世界,最終感受世界。而這也是《生命之詩》裡「詩(poetry)」所具備的意義,因為在寫一首詩之前「必須認真地觀察」。同樣地,美子的變化是出自於「看」,也就是說,透過她看孫子的視線,或是老男人苦苦哀求她想在最後當一次男人,而她最終答應時看著他的目光;又或者是她和被害少女的母親閒聊甜杏時的眼神。透過這些視線,使她產生變化。
如同《密陽》中的基督徒藥師所斷言,信仰讓人類得以接觸看不見的世界。然而李滄東電影所暗示的「看不見的世界」,並不是為了純粹想尋求慰藉的個人而準備的海市蜃樓,它指的是一個永遠到達不了的虛擬世界,這在《燃燒烈愛》,一部講述階級間差距,以及不信任而造成悲劇的最新作品中也不斷浮現。而這個「看不見的世界」,只有那些為求對現實異常敏銳的感知、堅毅不拔的電影工作者才能捕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