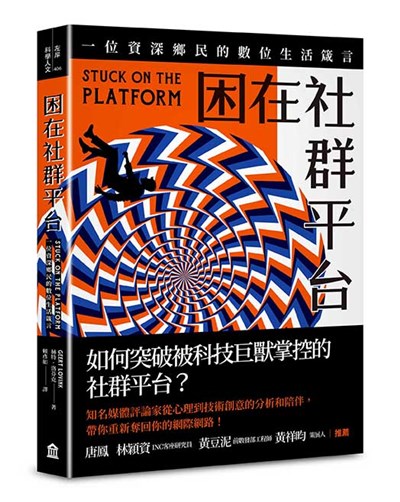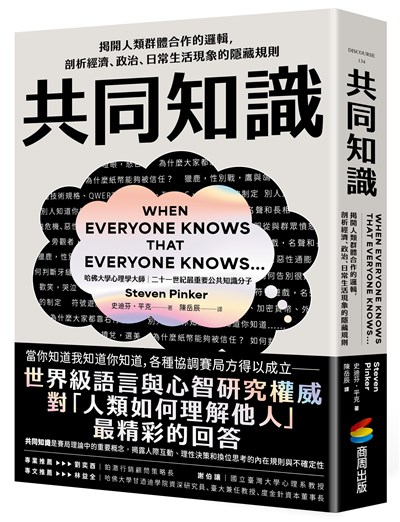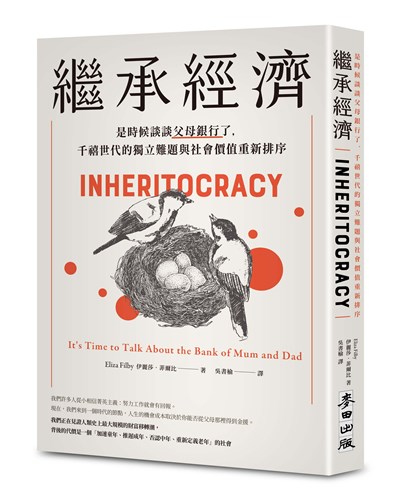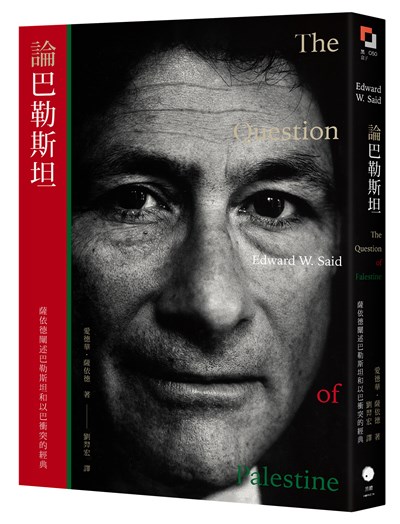吳耀忠是台灣當代文化發展上的重要藝術家,於1987年英年早逝,享年五十歲。在國立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支持下,駐校作家林麗雲與研究員蘇淑芬、清大社會所陳瑞樺組成團隊,到處尋找吳耀忠留下的畫作,並寫成以《尋畫》為書名開頭的兩本書,讓世人瞭解這位本土藝術家的生命故事。
吳耀忠不把畫看成商品,畫作若非贈送親友就是存放家中,身後畫作遭竊流入藝術市場,家人獲知後,將家中留存的八十餘幅油畫與其他素描、水彩、蛋殼畫一併捐贈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2009年,林麗雲受聘交大後,進行吳耀忠的報導文學調查寫作,因而陸續找回一百三十餘幅畫作,並邀持畫者寫下收存吳耀忠畫作的故事,再集結出版《尋畫: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書畫冊。
林麗雲同時把如何找到吳耀忠畫作持有人,以及這些人如何回憶吳耀忠,做詳盡的記錄和說明,等於集體為吳耀忠寫傳記,就是《尋畫:吳耀忠的畫作、朋友與左翼精神》一書,不僅呈現吳耀忠與其朋友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他以人道關心勞動者和對社會公平的熱情付出,也讓大家了解,他之前畫風較像他的老師李梅樹,後來則都是素樸、關懷勞工的寫實畫作的原因。
由於理想性格與人道關懷的信念,使他接觸社會主義左翼思想,而於1968年被捕入獄,1975年出獄後,一度主持一家藝廊,後來又因藝廊改組與藝壇趨向商業化,使他受不了而長期借酒澆愁,以致肝硬化病逝,也提醒大家世間幾乎已經遺忘的信念。翻閱這兩本書,看到在他處難以再見到的勞動者畫像,精確而充滿感情,你會了解吳耀忠在台灣美術史上的特殊地位。
文章節錄
《尋畫: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尋畫:吳耀忠的畫作、朋友與左翼精神》
關於畫作與詩作「向日葵」
我在陳映真的小說《將軍族》封面上,看到一幅以墨綠為底色調的油畫《年輕的補鞋匠》,封面畫家署名「吳耀忠」。在七○年代中期,這是一本被查禁的書。那時我讀高中,只知道陳映真曾做為思想犯入獄,卻不知道為什麼。畫在禁書封面上的那油畫,也因此具有一種社會底層的慘綠、壓抑和灰黯。然而,那年輕鞋匠的神情中,仍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專注認真以及尊嚴,畫家對人物的愛,直穿筆端,讓你總要想到補鞋匠的生活和未來,而多了一點深情的注視。
吳耀忠,我記住這名字,並且將他和陳映真被查禁的書連在一起。那一年約莫十七歲。—摘自《尋畫: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楊渡〈關於畫作與詩作「向日葵」〉
三鶯大橋的兩端
陳映真與吳耀忠結識相當早。小學畢業,陳與吳同年考上位於台北的成功中學初中部,陳住鶯歌、吳住三峽,中間隔著三鶯大橋。當年,前往台北就讀只有火車一途,車站設在鶯歌,吳必須從三峽與人合搭輕便車或是步行四十分鐘,抵達鶯歌站後再轉搭火車到台北,因此陳與吳雖然分屬丙班和乙班的不同班別,但兩人卻經常在鶯歌車站月台上一起等火車上學,他們是這樣認識的。
但兩人真正結成好友則是在初三那年。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七日,陳映真在吳耀忠的告別式上追憶好友時說:「有一次台北的幾位同學來找我,後來我們一起到鳶山下的鳶潭邊露營,就在那時候,他因為就近也來了,我記得就在那天晚上,我們在營火邊坐了一個晚上,也聊了一個晚上,當然,那時候都很幼稚,可是就在那個時候,我們成了莫逆之交。」在〈鳶山〉一文中,陳映真繼續寫著:「三十五年之後,他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我說過,幼稚的、青澀的夢,無謂的句子。」初三那年陳映真留級一年後考上成功中學高中部,而吳耀忠則在初中畢業後考進位於台北的大同高中繼續學習。根據陳映真的追憶,高中三年兩人疏於往來,唯一一個印象就是吳耀忠病了。
吳父留日學醫,返鄉後在三峽老街上開了牙醫診所,吳耀忠是家中長子,身負長輩厚望,然而敏感、纖細的吳耀忠,當時卻沉迷於先秦諸子的學說論述。吳耀忠的大妹吳明珠在受訪中也提到,高中三年,吳耀忠的成績不算好,除了會畫畫外,理化、數學都不行。但隨著聯考大限的逼近,一方面擔心辜負家人期待,再方面又憂慮考不上大學就必須入伍當兵,如此的苦惱加上種種的壓力,高三那年吳耀忠終於病倒了。療病期間,吳耀忠曾經央求家人代尋一處清靜住所,但因吳的病情反覆不定,最後家人只好將其送往台大精神病院觀察治療。
說也奇特,那件事對於曾經友好但當時已有些疏離的吳耀忠和陳映真而言,竟然像默片般地存印腦海。一九七八年,在《雄獅美術》的安排下,陳映真以許南村之名對吳耀忠進行專訪,該訪問稿刊登於同年八月的雜誌上,訪談中他們都提到了這段往事,陳映真說:「然而,一個永遠在我心中那麼鮮明的記憶迅速地呈現在我眼前。那一年,對於我們都是不幸的一年。那年夏天,養父咳血去世。第二天,我在屋前呆坐的時候,一輛台車緩慢地由一個台車伕推過門口街上的台車軌道。一個面容蒼白的少年,被神情憂愁的父母圍坐台車上。」當時陳心中驚異地喊道:「耀忠」。陳繼續說:「燠熱的六月的陽光,喪父的悲哀、緩慢地滑走在軌道上的台車、耀忠的青蒼的臉神⋯⋯構成不易遺忘的圖面,深藏在我的記憶裡。後來,我才知道那是你到台北住院的早晨。」至於當時坐在台車上的吳耀忠則是:「即使在病中,我也看見你家門前新搭的帳棚,恍惚中也有不祥的疑惑。後來才知道你父親去世了。」
一九五七年,陳映真自成功高中畢業後旋即考進淡江英語專科學校︵今改制為淡江大學︶外文系,而吳耀忠則因療病期間得到院中一位護理人員的鼓勵,不僅脫離鬱悶病困並且重拾畫筆。聯考失利後的吳耀忠,進入補習班準備第二年的大考,而就在這一年,陳映真與吳耀忠再續前緣,情誼比往日更加緊密。在接受陳映真的訪問時,吳耀忠就提到:「你應該記得我們倆,有一陣子,各自拿著速寫本子,在火車站,在街角,熱情洋溢地練速寫⋯⋯」而陳映真在〈鳶山〉一文中則是如此地寫著再度見到吳時的印象:「等我們再聚,我已是外文系學生,而他則是蓄著長髮的,俊美英發的年輕藝術家,窩在補習班裡準備學科,等著考進師大美術系。」
一九五八年,陳映真陪著吳耀忠一起報考三年制的「省立師範大學文學院藝術學系藝術專修科」,吳耀忠取得榜首而陳映真敬陪末座。此後,吳耀忠成為陳映真眼中:「一個非常狂飆、熱情、反叛、浪漫的學生,當別的同學在談戀愛、喝酒、混日子的時候,他卻像發瘋一樣每天都在畫畫。」而陳映真則留在淡江英專繼續他外文系的大學生活,漸漸成為一名影響整個世代的小說家。如果沒有那場翻天覆地的「民主台灣聯盟」案,一名畫家和一名作家的情誼,該會發展出甚麼樣不同的故事呢?
關於陳映真的社會主義信仰,在他個人的自述以及他人的分析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但吳耀忠呢?如果根據陳映真的說法,只知道大學時期,兩人一起閱讀從舊書攤買回來的各式各樣禁書,包括中國三○年代的左翼小說、舊俄時期的現實主義藝術論等;還有,他們也都一樣喜歡魯迅並且心中嚮往新中國。如果其中一定要細究這件事上到底是誰先起了頭,那也只能確定的說,成立讀書小組應該是由陳映真提出來的。刊載於二○○四年《上海文學》第一期的〈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一文中,陳映真就提到:「就跟所有的思想過程一樣,思想發酵到一定程度,就會產生一種實踐和運動的飢餓感,就是覺得老這樣讀書,甚麼都不做,很可恥。然後我又不敢把這樣的思想告訴別人,但每一個青年都有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我就跟最要好的畫家吳耀忠(已過世),形成了一個很小的讀書小圈子,後來當然被國民黨特務滲透,很便宜就把我們賣掉了,坐了幾年牢。」─摘自《尋畫:吳耀忠的畫作、朋友與左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