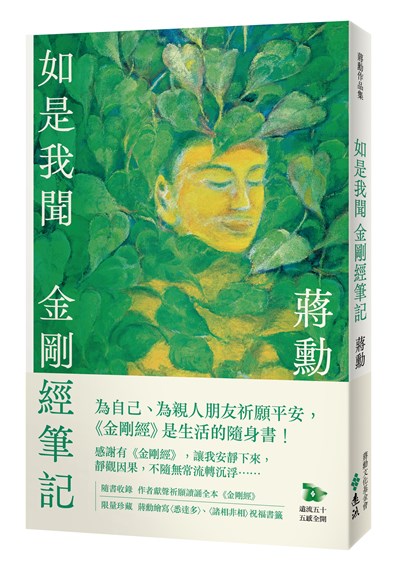核能發電災害難以掌控及貽害萬年,令人對核能愛恨兼具,近者有日本今年三一一地震海嘯引發的福島核災,後遺症還難估計,但1986年發生的俄羅斯車諾比核災,則是核災史上之最。記者出身的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在車諾比災變二十五年後,以訪談受害人的敘事文學方式,記錄這場最慘烈的核災帶給人們的身心靈傷害。
車諾比核災事件發生第一時間俄國不講,歐洲發電廠卻偵測到不尋常的訊息,數據則從看不出影響層面很大的最初死亡三十一人,到後來達數十萬人甚至數百萬人受害。作者花三年時間訪談受害者、科學家、當時政府官員,以報導文學呈現核電廠爆炸帶來的長期悲劇,讓大家了解,核災不是立即殺死人,是殺死人的未來。
書中指出,核災初期,一位消防隊員送醫,他的妻子賄賂進醫院陪伴丈夫,目睹丈夫潰爛的皮膚被棉被割傷,死前咳嗽咳出的內臟竟是破碎的;政府規定已有小孩的婦女不能再生小孩,在車諾比村撤村後,小孩在學校被歧視地稱「車諾比人」,後來許多人生下畸形嬰兒,一個嬰兒竟有一張延長至耳朵部位的大嘴卻沒耳朵。
當時有政治權力的行政官員、媒體與醫生都配合政府說謊。例如找國家報記者去拍照,卻是虛構場景,找一對新人去拍結婚照,宣傳沒問題了,其實問題還很大。一些科學家說,政府當時該做的事都沒做,還不給人民有關身體輻射超量後果的知識,例如未把碘注入水庫,減緩人民的輻射症狀,人民則不懂也買不到碘,人民到醫院偵測輻射量,醫師與軍人都隨便敷衍,政府還不准賣輻射偵測器。
作者指出,車諾比核能反應爐外殼已毀,現做石棺包裹著,但爐心至今還在放射,若遭地震震出裂縫仍會外洩,而輻射元素半衰期長達數千、數萬年,遠超過人能掌控的程度。書中內容實在太震撼,記錄片也拍不出來,擁核者看了此書應會改變觀念,人類也應停止核能發電,尋找其他替代能源,歐洲人現在晚上多用輔助能源,不再燈火輝煌,德國宣佈不再發展核電,丹麥、瑞典發誓到2020年發展出可替代性的再生能源,台灣也在努力節能減碳,但還有很大的空間有待努力。
文章節錄
孤單的人聲
醫生不知道我晚上在生物室陪他,是護士讓我進去的。起初他們求我:「妳還年輕。為什麼要這樣?那已經不是人了,是核子反應器,妳只會和他一起毀滅。」但是我像小狗一樣在他們身旁打轉,到門口站好幾小時,不斷懇求,最後他們說:「好吧!不管妳了!妳不正常!」早上八點,醫生開始巡房前,護士會在帷幕外喊:「快跑!」我就去宿舍待一個小時。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我有通行證。我的小腿腫脹,變成藍色,我實在累壞了。
他們趁我不在的時候幫他拍照,沒有穿任何衣服,赤裸裸的,只蓋一小片薄布,我每天替他換那片布,上面都是血。我把他抬起來,他的皮膚黏在我手上。我告訴他:「親愛的,幫我一下,你自己用手臂或手肘盡可能撐著,我幫你理順床單,把皺的地方弄平。」床單只要稍微打結,他的身上就已經出現傷口,我把指甲剪得短到流血,才不會不小心割傷他。沒有護士可以接近他,他們需要什麼都會叫我。
他們替他拍照,說是為了科學。我放聲大叫,把他們推走!捶打他們!他們怎麼敢這麼做?他是我一個人的──是我的愛,真希望可以完全不讓他們接近他。
我離開房間,走向走廊的沙發,因為我沒看到他們。我告訴值班護士:「他要死了。」她對我說:「不然呢?他接收到一千六百侖琴的輻射,四百侖琴就會致人於死,妳等於坐在核子反應爐旁邊。」都是我的……我的愛。他們都死掉之後,醫院進行「大整修」,刮掉牆壁,挖開地板。
到最後……我只記得零星的片段。
那天晚上我坐在他身旁的小椅子上。八點鐘,我跟他說:「我去散個步。」他睜開眼睛又閉上,表示他聽到了。我走到宿舍房間,躺在地板上,我沒辦法躺床,全身都好痛,清潔婦敲我的門說:「快去找他!他像發瘋一樣一直叫妳!」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諾克拜託我:「陪我去墓園,我沒辦法自己一個人去。」維特亞.克比諾克(Vitya Kibenok)和沃洛迪.帕維克要下葬,他們是我的維斯里的朋友,我們和他們兩家很要好。爆炸前一天,大家在消防局合拍了一張照片,我們的丈夫都好英俊!好開心!那是另一種生活的最後一天。我們都好快樂!
我從墓園回來後,馬上打電話到護理站問:「他怎麼樣?」 「他十五分鐘前死了。」什麼?我整晚待在那裡,只離開三個小時!我對著窗戶大叫:「為什麼?為什麼?」我朝天空大喊,整棟樓都聽得到,但是沒有人敢過來。然後我想:我要再看他一眼!我跑下樓,看到他還在生物室,他們還沒把他帶走。他臨終前最後一句話是:「露德米拉!小露!」護士告訴他:「她只離開一下子,馬上回來。」他嘆了口氣,安靜下來。我後來再也沒有離開他,一路陪著他到墓地。雖然我記得的不是墳墓,是那只大塑膠袋。
他們在太平間問我:「想不想看我們替他穿什麼衣服?」當然想!他們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沒辦法穿鞋,因為他的腳太腫了。他們也必須把衣服割開,因為沒有完整的身體可以穿,全身都是……傷口。在醫院最後兩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覺骨頭晃來晃去的,彷彿和身體分離。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從嘴裡跑出來,他被自己的內臟嗆到,我用繃帶包著手,伸進他的嘴裡拿出那些東西。我沒辦法講這些事,沒辦法用文字描寫,甚至覺得好難熬。都是我的回憶,我的愛。他們找不到他可以穿的鞋子,只好讓他赤著腳埋葬。
他們當著我的面,把穿著制服的維斯里放進玻璃紙袋,再把袋口綁緊,放入木棺,然後又用另一層袋子包住木棺。玻璃紙袋是透明的,厚得像桌布,最後他們再把所有東西塞進鋅製棺材裡,只有帽子放不進去。
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來了,他們在莫斯科買了黑色手帕。特別委員會召見我們,他們的說辭都一樣:我們不可能交出妳的丈夫或你的兒子的遺體,他們都有強烈輻射,要用特別的方式──密封的鋅製棺材,上面蓋水泥磚──安葬在莫斯科公墓,所以你們要簽這份文件。
如果有人抗議,說想把棺木帶回家,他們會說,死者是英雄,不再屬於他們家了,他們是國家的英雄,屬於國家。
幾個軍人和我們坐上靈車,包括一名上校和他的手下,他們等待指令行事。我們在莫斯科環城公路繞了兩、三個小時,又回到莫斯科,他們說:「現在不能讓任何人進入墓園,墓園被外國記者包圍了,再等一下。」兩家父母都沒有說話,媽媽手裡拿著黑色手帕。我覺得自己快昏過去了:「他們為什麼要躲躲藏藏?我的丈夫是什麼?殺人犯?罪犯?我們要埋葬什麼人?」媽媽摸摸我的頭說:「女兒,安靜,安靜。」上校說:「我們進墓園吧,妻子歇斯底里了。」我們到了墓園,那些士兵負責抬棺木和包圍、護送我們,只有我們可以進去。他們不到一分鐘就用土蓋好棺木,上校在旁邊大喊:「快一點!快一點!」他們甚至不讓我擁抱棺木。接著我們就被送上巴士,整個過程都偷偷摸摸的。
他們馬上幫我們買好回程機票,隔天就出發,從頭到尾都有便衣軍人跟著我們,不讓我們離開宿舍購買旅途要吃的食物,也不讓我們和別人交談,尤其是我,好像我當時有辦法說話一樣,其實我連哭都哭不出來。離開時,值班女工清點物品,她當著我們的面疊好毛巾和床單,放進聚乙烯袋,很可能準備拿去燒掉。我們支付宿舍費用,十四個晚上,那是治療輻射中毒的醫院,十四個晚上,一個人在十四天內死掉。
回家後,我一走進屋子就跌到床上,整整睡了三天。救護車來了,醫生說:「她會醒的,只是睡了一場可怕的覺。」
我當年二十三歲。
──露德米拉.伊格納堅科,已故消防員維斯里.伊格納堅科(Vasily Ignatenko)遺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