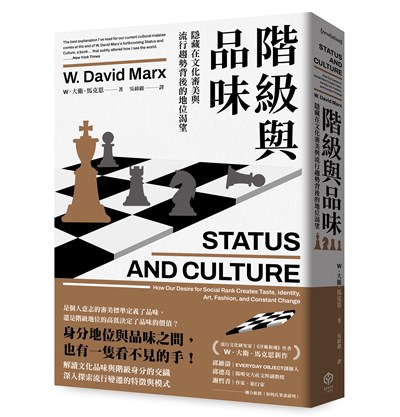日本爸爸和台灣原住民媽媽在國際聯姻頻繁的現代不算特別,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就有特殊意義,《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一書,不僅書中人物際遇充滿傳奇,書的出現也很傳奇,這些傳奇不被一般台灣人熟知,卻應屬於台灣歷史的一環,讀者閱讀後難免唏噓!
作者下山一的日本父親來台擔任總督府警察,奉命到山區理蕃並娶泰雅族公主,以控制台灣原住民,而展開日本爸爸、泰雅媽媽的家族故事。下山一後來娶日本女子,日本戰敗後,雖符合遣送回日資格,但涉及謝雪紅案被國民黨追捕,逃亡山區,遣送令一直到不了他手上,他趕不上遣送的船隻,又沒錢買船票,只好留在台灣,因子女教育與種種因素,他與妻子決定歸化中華民國籍,並改漢名林光明。
經歷坎坷的林光明營生困難,五個子女未曾學過日語。女兒下山操子,漢名林香蘭,師範畢業擔任教職後,家庭經濟才穩定下來。林光明對於父母和自己的複雜經歷有很多記憶,一喝醉酒就講不停,但孩子聽不懂,長年在南投任教的林香蘭十幾年前罹患血癌,走過生死關頭後,決定開始學日語,寫下父親所說的故事,整理成書。
書中描述未能離台的日本人在台灣的生活與心情掙扎和他眼中所看到的台灣,非常有價值;也提到日本據台時的理蕃政策與原住民民俗,如作者小時候見識過日本主導泰雅族出草獵取另一蕃社人頭的人頭祭及他與霧社事件抗日的莫那魯道有間接關連;都提醒讀者,我們對台灣的認識和了解仍有缺縫,可從各種角度探索彌補。
文章節錄
《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
記憶之河回溯到我的幼年時代:
我的爸爸是日本巡查,名叫大塘正藏。爸爸媽媽都非常疼愛我,每晚我都要含著媽媽的奶頭才能入眠。我們家還有一隻中型白色長毛狗叫博基、一隻白色的波斯貓,都睡在同一個房間裡。屋後菜園邊,還有爸爸最喜愛的鬥雞,牠們都是我們孩子們的好玩伴。
我最懷念的童伴是,大我三歲被稱大劍客的神之門豐,和大我三個月的二劍客鈴木實,我是小劍客,我們常常模仿父親和一個漢人警丁、一個蕃人警丁叔叔練習日本劍的模樣,揮舞著木棍,大人們都稱我們為「三劍客」。
我們住在台灣中央山脈接近合歡山峰的馬利可彎分遣所內,這裡的海拔約二千三百公尺,整個分遣所內就只有三家九口人和兩位警丁叔叔,總共十一人住在這裡。當時分遣所被鐵絲網圍繞,鼻子若聞到烤肉味,大人就會把我們三個孩子拉去瞧瞧,然後指著焦黑冒煙的動物或蕃人屍體說:「絕對不許碰觸鐵絲網,不然就會像那屍體一樣成為焦黑鬼怪。」
鐵絲網外面到處埋著地雷,有時可看到動物和蕃人踩踏地雷炸得粉身碎骨的慘狀,所以大人們嚴禁我們步出鐵絲網外。長大後才得知鐵絲網平常天黑就通電,遇非常狀況則日夜都通電。這是為了保護分遣所內的人員和儲備的彈藥武器的措施。
可惜好景不長,大劍客的爸爸調職,他們全家下山到豐原了。剩下我們同齡的二劍客。不久鈴木實因為疑似感染禽流感過世,分遣所內的孩童僅剩孤零零的我。
從此我鬱鬱寡歡,白天還可以和博基、咪咪、鬥雞相處,半夜都怪叫亂踢打:「鬼!鬼!爸爸媽媽救我!」接著整日發高燒,囈語不斷,偶爾全身顫抖抽搐,爸爸媽媽懷疑我被阿實感染了禽流感,請公醫來診治,他說:「是感冒加上驚嚇過度造成的。」針藥無效,我陷入了昏迷狀態。
當我睜開矇矓的雙眼,不知自己置身何處,身邊圍繞很多陌生但關愛的眼睛,惟獨不見爸爸、媽媽。突然間我看到阿實,於是就高興的坐起來:「阿實,太好了,你終於回來了。」仔細端詳那張憨笑的臉,不對!他的年紀比阿實小,眼睛又比阿實的大。而那個額頭有刺青,以十分慈愛的手愛撫著我的婦人是誰?那個留著八字鬍,手抱圓臉圓眼美麗小女孩的男人又是誰?
我不禁大聲叫:「你們是誰?這裡是哪裡?我的爸爸、媽媽在哪裡?爸爸、媽媽救我呀!」
爸爸和媽媽笑容可掬地出現,我立刻躲進媽媽懷裡。
爸爸帶著既高興又感傷的語調說:「阿一,你不是我們親生的孩子,馬烈巴駐在所下山治平主任才是你親生的爸爸。」手指著八字鬍男說。又手指紋面女,「貝克‧道雷夫人才是你親生的媽媽。這位叫阿宏,是你的弟弟,那位叫敏子,是你的妹妹。」(摘自《流轉家族》第三話「日本爸爸與泰雅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