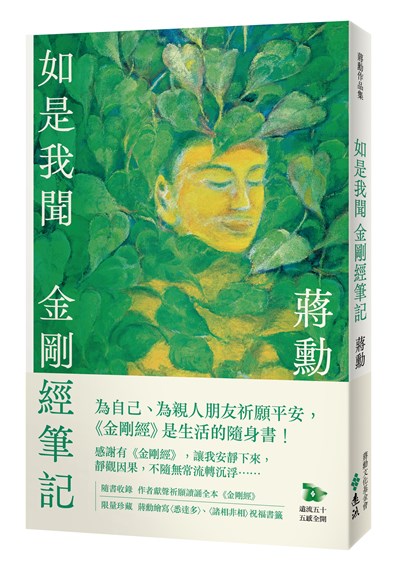一九六四年六月到八月,美國近千名白人在密西西比州參與為黑人爭民權的「自由之夏計畫」社會運動,引發的效應遍及全美國,影響了後來的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學生運動等社運。史丹佛大學社會學者道格‧麥亞當投入黑人與民權發展的研究多年,在《自由之夏》一書中,分析那年夏天社運志工與社運的關連性。
作者原來想了解「自由之夏」對往後多場民權運動有什麼啟發,但在深入研究後,轉為研究「自由之夏」社運志工為什麼要投入這場民運,並訪問志工當事人四百餘人,結果發現他們大都來自中產階級甚至更高階社會家庭,經濟條件不錯,使他們有極高自信與理想,相信自己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分析指出,「自由之夏」社運之所以進行得轟轟烈烈,與參與志工的理想性格有很大關連。一九六0年代初期,許多黑人仍遭到不平等對待,也沒有投票權,白人志工要為黑人爭民權,必須背負很大壓力,包括白人極端份子會恐嚇他們,黑人社區極端份子也未必歡迎他們,理想性格讓他們有勇氣堅持下去,同時陸續投入美國六、七0年代的各種社運甚至環保運動。
「自由之夏」是美國歷史上著名的社會運動,這本書整理出相當完整的史料,包括紮實的當事人訪問資料,顯出當年大眾傳播媒體強調學生志工因個人「年輕的叛逆」才參與社運的報導有偏差。作者的調查研究分析可以提供讀者面對本土的社會運動時,有很好的借鏡與反思。
文章節錄
序幕 尋找志工
每一天發生的每樣事對我來說都是全新的。資訊不斷轟炸著我,經驗不斷轟炸著我……而我衰微的精神狀態幾乎要失控了。
你感覺自己將參與這歷史性一刻;在一區域中,整體生活模式裡很深刻的某項東西即將轉變……你正在……創造……歷史。從某些方面來看是全然無私無我,但(你)也同時發現了自我。
在我生命中,就社會改革的願景來說,它是我將經歷過最有可能成真的經驗……就參與歷史來說,它也是我將擁有的經驗裡最棒的一次,但是它……也讓我付出了代價……(情緒上)它讓我受挫……(幸運地是)我的身體並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因此,至少就肉體層面來說,我……活了下來。
(它)是極具啟發性的。我的意思是,我覺得整件事情……開始去思考身為一個女性,我該怎麼做,還有……我該怎麼過我的人生。我要成為一位專業人士嗎?我要去讀法學院嗎?……如今的我,有太多必須回溯到它。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有太多必須回溯到我對那段時期的回憶。
它讓我欣喜若狂……第一次這些片段碎塊嵌合在一塊……感覺像我自己……我認為透過它,我們不但成就了些事,也是實現我個人的救贖。
它是我人生中最長的夢魘: 三個月── 一九六四年的六月、七月、八月(Sell ers,1973 : 94)。
以上所有人口中所謂的「它」究竟指的是什麼?是什麼樣的共同經歷,讓這麼多人產生了如此分歧卻又深刻的反應呢?這個我們所關注的事件就是一九六四年密西西比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運動,或依當時為人所知的名稱,叫做夏日計劃(Summer Project)。
由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 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以下簡稱SNCC)領頭的這項計劃,歷時不到三個月,自六月初至八月底止。在這段期間,有超過一千人──絕大多數是北方白人大學生──啟程前往南方,到當地執行計劃,整個運動由四十四個這樣的子計劃組成。在密西西比的日子裡,這些志工共同居住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s),或寄住在那些不懼種族隔離主義者暴力威脅的當地黑人家庭中。平時他們得擔負許多任務,主要是為黑人選民進行登記,以及在所謂的自由學園(Freedom Schools)裡任教。
在以上的概述中,略而未提的部分,就是那難以被緩解的恐懼、令人苦惱的貧困, 以及間或發生的暴力事件,這些都再再困擾計劃的進行;其加總的效果,也讓這個夏天成為幾乎每位參與者心中難以磨滅的經驗。
有三位參與者──錢尼(James Chaney)、古德曼(Andrew Goo dman)及史維納(Michael Schwern er)──甫加入計劃才十天,就被一群由密西西比執法人員帶頭的種族隔離主義者綁架, 三人被痛毆至死。隨後搜索他們行蹤的行動,把許多聯邦調查局探員及數百名記者引到該州。儘管有他們的出現,暴力事件仍層出不窮。
另一位志工在夏季接近尾聲之際喪命,還有數百人遭受炸彈攻擊、被毆打或逮捕。這些志工接觸到了新的生活方式──跨種族的人際交往、共同居住的生活、更開放的性關係──新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批判美國的嶄新觀點,據此他們經驗了一種自由解放的意識。總而言之,它是這群傑出的年輕人所擁有的一段非凡夏日,其影響持續不輟,不論是對這些志工,或整個國家。
夏日計劃初期,它充分反映美國六0年代早期那種典型自由派理想主義色彩;儘管仍存在某些緊張與矛盾,但這個計劃確實體現了構築該時代進步願景的部分理想,包括跨種族主義(interracialism)、非暴力及自由/左派聯盟(liberal / left coalition)。因此,我們也從這些志工身上看出這些理想。
身處夏日運動開始前夕,計劃參與者所象徵的是六○年代初,旭日東昇的理想主義中「最棒且最光明的一面」。這群極高比例來自菁英學院及大學的志工,朝氣十足,大多學業表現突出,積極參與政治事務,並充滿高度熱忱致力於徹底實現理想主義之價值,他們自小被稱為是美國之根基的那些價值教導。大體說來,他們信奉自由主義,但不走基進(radical)路線;他們是改革主義者,但並非革命家。
然而,不管是志工或這個國家,很快地將經歷一番劇烈的轉變。身為同一國家之民,我們在時間長河裡流轉,自新疆界(New Frontier)的光輝歲月跌落至這個動盪不安的六0年代晚期。如果自由之夏算是六0年代初自由主義的全盛時期,它所仰賴的根基卻在不久之後傾覆。
不到一年後,跨種族主義就在黑權主義(black power)與黑人分離主義的呼聲中壽終正寢。在一九六五年華茲(Watts)事件的啟示下,非暴力的主張也廣被仿效,起碼在運動的宣傳上是如此。自由\左派聯盟同樣也無力在這個夏天後延續下去,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為它劃下句點,當時民主黨的中堅人士選擇授予席次給排除黑人的密西西比代表,而不是夏日計劃的挑戰代表。
與整個國家一樣,這些志工也受到當時的紛擾亂象影響。因六0年代中期至晚期的種種事件,讓絕大多數的人都變得更加基進。其中有很多人,在這些事件上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實際上,沒有人是不受那些事件影響的。
本書的中心論旨是,若想徹底了解那個時代,這些志工與美國所經歷的劇烈轉變,我們必須認真重新評價這場自由之夏。畢竟,不僅對這些參與運動者的生命,還有整個新左派陣營來說,自由之夏都象徵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其重要性在於這個夏天發生的種種事件,以及隨後引發的文化與政治效應。這個夏天發生的種種事件有效地再社會化、激進化這群志工,而他們與其他志工所建立的連帶,又進一步為社會運動者的全國性網絡,奠下基礎,此網絡日後孕生了這個時代其他的重要運動,包括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學生運動。
簡而言之,自由之夏不僅為六0年代眾多行動主義(activism)的嘗試提供了組織上的基礎,同時也頗具關鍵性地推動了這個時代茁生的反文化思潮之發展。因此,本書回溯敘述自由之夏計劃,也重新衡量它對志工,及整體美國社會所造成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