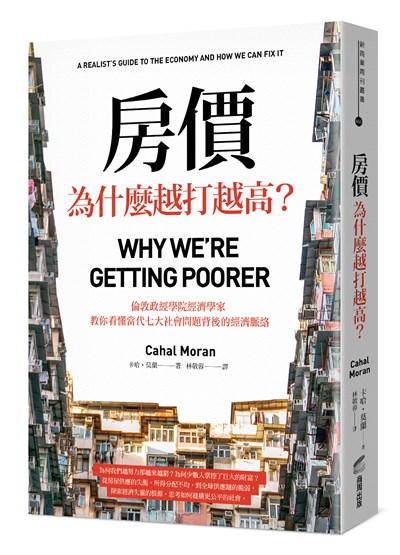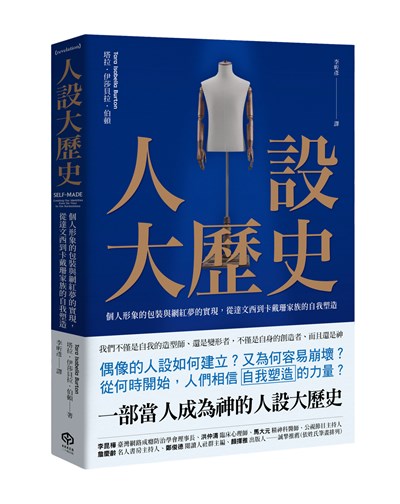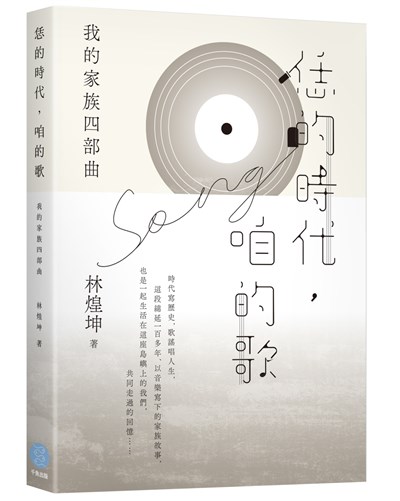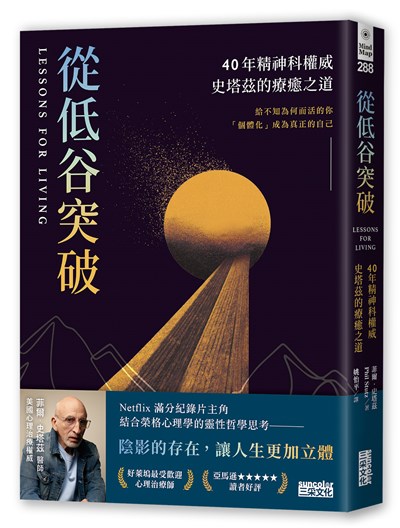走路是一個哲學行動,一種心靈經驗,一種對簡樸生活的肯定,對簡單事物的喜悅。本書不但是思想精煉、文字優美、引人遐思的哲學散文,葛霍更以妙筆生花的文字,在扉頁之間為「走路的藝術」做出扣人心弦的定義。在科技時代裡,人類也許只有憑藉雙腳,才能擁有真正的思考。當我們邁出步伐,在身體的動與靈魂的靜之間沉澱思緒,將能從孤獨中體驗「走路」的哲學之趣。作者筆下的文字澄淨、簡潔、精細,行文優美至極,閱讀本書定可體會到走路的奧妙與樂趣。
文章節錄
《走路,也是一種哲學》
寂靜
正如孤獨有好幾種,寂靜也有好幾種。
真正的走路總是寂靜的。當然,每當我們離開街道、公路、公共場所(那其中的速度、衝撞:熙來攘往的步履敲擊地面,叫喊、交談、低語如聲浪排山倒海,引擎的尖銳噪音響徹雲霄),我們立刻又感受到無庸置疑的寂靜,一種來自原初的清明。一切都安詳、專注、閒適。我們擺脫了世人的喋喋不休,走道上的雜沓聲響、漫天飛舞的謠言。走路。寂靜扣人心弦,耳朵彷彿進行著遼闊無疆的呼吸,我們浸淫在通透的寂靜中,宛如一陣大風吹走所有雲霧。
有一種寂靜是森林的寂靜。樹叢在我們周遭構成移動的、輪廓從不確定的高牆。我們走在林間小徑,沿著狹窄的泥土路蜿蜒前進。我們很快失去方向感。這時的寂靜顫動著,令人不安。
有一種寂靜是夏日午後,在山壁上、石路中,頂著火熱的大太陽,步履沉重的寂靜。白花花的、礦物性的、壓垮人的寂靜。我們只聽到石塊嘎吱摩壓的聲響。毫不留情的、已成定局的寂靜,彷彿透明的死亡。天空藍得何等漠然。我們低頭前行,偶而含糊地嘟嚷出一些聲音,讓自己安心。萬里無雲的晴空、灰沉沉的岩壁,紮實飽滿地充斥在周遭,一片沒有任何東西能超越的寂靜。極致的寂靜,靜止而又振動,緊繃得有如一把弓。
有一種寂靜是黎明前的寂靜。秋天,當路途遙遠,我們很早就得出發。外頭一片深紫,幽微的光線匍匐在黃紅色的樹葉下。這是一種聚精會神的寂靜。我們輕輕走在大樹的黑影中,看深藍的夜色還輕柔地攬著它的身軀。我們幾乎害怕清醒過來。萬物正在微弱地耳語。
有一種寂靜是走在雪地裡的寂靜。白茫茫的天空下,步履陷入雪中,寂靜無聲。四周沒有任何動靜。事物、時間,都被凍結在冰雪中。一切都停頓下來,凝結在喑啞的靜止狀態中。一切都均勻、單一、鬆柔如毛氈。這是一種待機狀態的寂靜,一段純白、懸浮、棉絮般的休止。
然後還有屬於黑夜的、獨一無二的寂靜。當夜晚降臨得太突然,或避難小屋距離還太遠,當我們必須在荒野中宿營,我們趕忙找到適當地點,生火取暖,填飽肚皮,很快進入夢鄉。幾個小時之後,夜正深,我們卻總會清醒過來。雙眼驟然張開,彷彿被寂靜的深沉攫住。我們稍一轉身,睡袋輕輕翻動,都造成不成比例的聲響。是什麼讓我們清醒?難道是寂靜本身的聲音?
在史蒂文森《偕驢旅行賽凡山》內〈松林中的一夜〉那個章節,他也提到這個忽然清醒的現象,時間大約是凌晨兩點,而且所有人只要在野外過夜,都會在這個時間有這樣的經驗。他在這件事中看到一個小小的宇宙奧祕:會不會是大地的震顫穿過我們的身體?會不會是一個夜晚加速的時刻?從遙遠星辰掉落的一滴看不見的露水?無論如何,那是令人心驚的一刻:寂靜聽起來毫無疑問像是音樂,或說在那個時刻,我們抬起頭,清楚聽到滿天星斗在歌唱。
走路時的所謂「寂靜」指的從來不是人聲喧囂嘎然而止時那種清靜。那種不知歇止的噪音像是一道屏幕,模糊了一切,宛如絆腳草般攻佔生命存在的遼闊草原。人聲喧囂震耳欲聾,令人頭昏腦脹,我們失了方寸,什麼也聽不到了。任何時候,雜音從四面八方襲捲而至,滿溢出來,淹沒一切,佔據所有空間。
重生與聖靈存在
在藉由走路獲得重生的烏托邦式理想中,我們可以舉信徒到岡仁波齊峰 朝聖的例子。這座終年積雪的宏偉山岳彷彿一座圓頂聖堂,巍峨矗立在遼闊高原上,在許多東方信仰中,它是一個聖地,是宇宙的中心。 如果朝聖者從印度的廣大平原地區出發,他必須步行數百公里橫越喜馬拉雅山脈,在冰凍的高山隘口和悶濕的低地山谷間穿梭前進。這條路極為費力,充滿高山地區的所有考驗和危險:險峻的步道、高聳的峭壁……行走途中,人逐漸失去自我認同及記憶,成為一具只是在不斷走路的軀體。
翻越一處埡口後,朝聖者抵達普蘭山谷,景物頓時改變,這裡是明亮而澄淨的礦物質世界。雪峰聳立於上的灰暗岩石區已經攀爬完畢,霧氣繚繞的墨綠冷杉林也已經全部穿越。在普蘭山谷,唯有大地與天空之間簡單而純淨的相互辯證。這是世界肇始的風景,一片由灰色、綠色和米色交織而成的荒原。朝聖者的個人歷史已經全然掏空,他穿過這片荒蕪的澄透世界,但他已經可以在遠方看到另一條山脈,線條規律有緻,閃耀聖潔光芒。他再也無足輕重,而他在黯黑的湖泊、泛著金光的山丘、故若磐石的大地中蜿蜒走行,在象徵意義上彷彿是基督徒進行的黑暗禮拜 。還要再翻越一處埡口,才能抵達諸神的境地。雪白圓頂不可思議的景象直撲朝聖者目光而來,使他益發勇往直前。岡仁波齊峰宛如一輪靜止不動的冰晶夕陽,那白雪皚皚的山頂超越人心,無可抗拒地引導、呼召著它。終於越過海拔超過五千公尺的古拉埡口,這時出現的景象令人震撼,彷彿持久不去的閃電深深穿透靈魂:無邊的偉大驟然、斷然展現。往下俯瞰是一座深藍色湖泊——瑪旁雍措(Manasarovar) ,而抬頭一望,岡仁波齊峰終於躍然眼前,它的身影宏偉雄大,卻又顯得如此自在而圓滿。在無比純淨的空氣中,萬物似乎都迸發光彩。聖山聳立在走路者身前,那是地球的臍帶,世界的軸心,絕對的中央點。面對此種令人暈眩的情景,朝聖者感覺自己既是征服者,又被完全征服。對所有用走路征服壯麗自然的人而言,任何絕對偉大的風景都在讓一股勝利的能量穿透全身的同時,卻令人感到全然被擊潰。兩股動能同時占據他的身心:他發出勝利呼喊,旋即崩潰落淚。他用目光主宰山岳,但那景象卻同時壓垮他。在這種相互矛盾的雙重動能中,走路者受到難以言喻的激盪。但對岡仁波齊峰的朝聖者而言,持續數月的去人格化過程所留下的虛空忽然在這裡被重新填滿:它在這裡,就在這裡,就在我身前!周遭數以千計的小石堆(用三塊、四塊、五塊石頭堆成的小小寶塔)使這種感覺更加強烈,它們見證著千百年來成千上萬的朝聖者跟他一樣,也體會過這種在筋疲力竭的時刻中感受到的狂喜。無以數計以礦石堆砌的供品散發出聖靈存在的氣息,彷彿從泥土中生長出來的永恆花朵,令朝聖者激動不已。他不禁渾身顫動,因為每個石堆似乎都在對他顯靈,他彷彿被無數鬼神團團圍住。
接下來他還要圍繞聖山走一圈,這要花上好幾天時間。在東方宗教傳統中,信徒到了一處聖地以後,必須一邊禱告一邊繞著它行走,而岡仁波齊峰儼然是一座天然神廟,一座由天神雕砌在冰原中的聖殿。但最終極的試煉正等著考驗朝聖者:他必須登上海拔五千八百公尺的卓瑪(Dolma)埡口,然後才盤旋而下,朝下方的山谷而去。抵達這種幾乎超過人類極限的高度以後,置身冰雪中的朝聖者停下腳步,像垂死者般匍匐在石地上,重新想起所有那些他不懂得愛的人,為他們祈禱。他與自己的過去達成妥協,然後毅然決然地與它告別。接著他下山前往「慈悲之湖」——托吉措(Gauri Kund),在翠玉般碧綠的湖水中洗去原有的自我認同和個人歷史。一個輪迴在此結束。朝聖者重生了,但他並非重生於自己,而是重生於自我的斷捨、時間的淡然,以及宇宙的大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