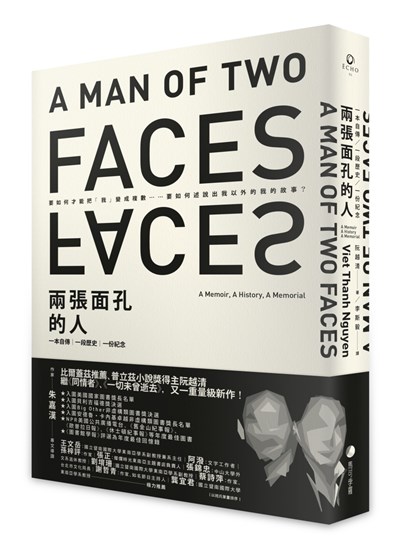911事件之後,哈伯馬斯與德希達兩位當代哲學思想巨擘在作者博拉朵莉的安排之下,進行了一場世紀對話。十二年過去了,這場哲學事件所觸及的問題,包括啟蒙理性與政治現實論、媒體與科技奇觀、恐怖做為一種政治因素、反恐與自體免疫暴力等,並未離我們而去。《恐怖時代的哲學》以精準優美的語彙讓這場哲學對話在華文閱讀圈裡再次「事件化」,必然成為公共論壇注目的焦點、更多創意與批判思考的觸媒。
文章節錄
《恐怖時代的哲學:與尤根.哈伯馬斯&雅克.德希達對話》
哈伯馬斯與德希達的哲學取徑完全不同,但似乎都追隨鄂蘭模式。他們和鄂蘭一樣(而和羅素不同),並不希望將政治參與視為哲學之補遺,或一個可供選擇、推遲或拒斥之「選項」。他們都是在20 世紀歐洲歷史的創傷脈絡中遭遇並擁抱哲學:殖民主義、極權主義和納粹屠殺。他們對於911 與全球恐怖主義的討論源自於同樣血脈。
哈伯馬斯和德希達的出生時間只相隔一年,1929 與1930 年,青少年時期都在二次大戰中渡過。哈伯馬斯住在德國,處於第三帝國無所不在的掌控下,而德希達則住在阿爾及利亞,當時是法國殖民地。
哈伯馬斯憶起自己和朋友們目睹紐倫堡審判時的深深震撼,當然還包括之後一系列紀錄片所暴露的納粹暴行,「我們相信,精神與道德的重整絕對必要,也無法避免。」然而要如何在一個擁有「無法掌控的過去」的國家中進行道德重整?這正是哈伯馬斯窮盡一生的漫長追尋,身為哲學家與公眾知識分子,他對此抱有超凡的執著與熱情。這項任務如此巨大,導致我們無法避免地讚歎:此人才能如此卓越,更曾受到世界各地學術機構邀請擔任教職,卻始終沒有離開德國,也沒有把「德國問題」從他的生命與思想舞台中央移開。畢竟從他身為「世界主義者」的角度來看,這種選擇也絕對合理。然而對我來說,正因為他沒有離開,所以讓我崇敬不已。他在歷史學家論戰(Historikerstreit )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正是哈伯馬斯投身公眾議題之深的絕佳證據。
到了1980 年中期,幾位德國歷史學家開始質疑納粹罪行的「獨特性」,因此出現一波修正主義者的解讀熱潮,意圖將納粹罪行等同於二十世紀的其他政治悲劇。哈伯馬斯對於柏林著名歷史學家恩斯特.諾爾特(Ernst Nolte)尤其震怒,他指出,「有關『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的文獻有一項明顯缺失。這些作者不清楚,也不願承認,除了使用毒氣的這項技術性細節外,納粹所做的一切早有人做過了,而且從1920 年代初期以來的文獻都有紀錄。」 諾爾特聲稱,納粹屠殺的本質和史達林的政治大清洗一樣,也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動亂一樣,差別僅在於「使用毒氣的這項技術性細節」。
在這場辯論中,哈伯馬斯是最雄辯的一人,他極力反對將德國歷史常態化,並強調德國亟需處理這段黑暗的過去。他也指出,面對納粹主義現實的「創傷性抗拒」自從第三帝國消亡後便一直在國內發酵,這種抗拒心態非常危險。在描述自己的世代時,他寫道,「二次大戰末期那代的孫兒已經長大了,但他們太年輕,無法親自體驗那種罪疚。然而回憶又已經隔了一段距離,」除去所有人的主觀看法,他的出發點仍然相同――「奧茲維辛中用以傾倒屍體的斜坡景象。」
罪疚不只屬於個人,責任也不只在你作出個人選擇時才出現。對此,哈伯馬斯和德希達看法相同,因為他們跟鄂蘭一樣,都是「後納粹屠殺時期」的哲學家。哈伯馬斯詳細解釋,罪疚與責任是如何深植於我們和他人的日常互動中:引用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話,稱此脈絡為「生活形式」(form of life)。
事實很簡單,納粹屠殺後的世代同樣成長於屠殺可能發生的「生活形式」中。我們的生活與整體生活脈絡相連;在此脈絡中,奧茲維辛同樣可能發生,而且不只是基於偶然條件,而是源自內在本質。我們的生活形式與父母及祖父母的生活形式相連──透過一個家庭、在地、政治且智識傳統的難解網絡──也就是說,我們是被歷史氛圍造就的結果。沒有人能逃脫此氛圍;因為我們的身分,無論身為個體或德國人,都和此氛圍緊密糾纏。
然而,任何人都不應該有所預設,以為哈伯馬斯既然突顯了歷史身為構成角色的重要性,表示他看輕參與政治領域的個人角色,或相信一個人的政治認同純然由歷史建構之傳統所決定。相反地,尤其是在德國的國族認同議題上,他為憲法愛國主義辯護。他認為,只有這種愛國主義,也就是基於每一位公民自發效忠於憲法的愛國主義,才可能形成不停進步的國族同盟。對於哈伯馬斯而言,德國人必須忠誠於共和國憲法,才能理解自己同為一個國家的國民,而不能執著於他所謂的「國族與社群命運之前政治基底(英文:crutches,法文:bequillie)。」
德希達親身體驗過這種「基底」的力量。1942 年10 月,他被本—艾柯農預科大學(Lycée de Ben Aknoun)退學;這所學校位於阿爾及利亞的比阿爾(El Biar)附近,也是他19 歲前的成長所在。他不是因為粗暴行為被退學,而是因為法國的種族法擴及其殖民領地,包括阿爾及利亞。對德希達而言,身分代表一整叢難解的界線。事後他痛苦地回憶,那個於1942 年被迫輟學的男孩「有點黑人血統,大部分是阿拉伯猶太血統,但本人對此毫無概念。沒有人向他解釋這件事,就連他的父母與朋友都沒有。」 德希達的背景突顯了身處於多重領域邊界之人所面臨的挑戰:猶太教及基督教、猶太教及伊斯蘭教、歐洲及非洲、法國本土及其殖民地,還有大海及沙漠。這也是德希達對哲學提出的挑戰。
在德希達回憶中,就在學校把他退學的那段期間,眾人使用的語言突顯了這些身分發言的複調性(polyphony):
在我家還有阿爾及利亞猶太人社群中,一般人很少說「割禮」,反而會說「受洗」;不說「成年禮」(Bar Mitzvah),反而會說「聖餐禮」。透過令人生懼的同化過程,伴隨而來的是軟化、鈍化的結果,這種痛苦我多多少少有意識到;那些無法言明的事件,感覺都在暗示我:不「天主教」、野蠻、令人討厭、「阿拉伯」、被閹割的割禮、被內化、且祕密地接受自己成為宗教儀式殺手的指控。
對德希達而言,無論是當時與其後的人生中,每個字詞都進一步衍伸為一整片歷史及文本連結而成的網絡,而他的政治介入行動則往往在彰顯這些隱藏的陸塊。只要我們無法反身地使用語言,我們就永遠無法意識這些網絡存在;這種「幸福的無知」的問題在於,因為仰賴此等網絡,我們甚至無法意識到自己在重覆許多規範性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