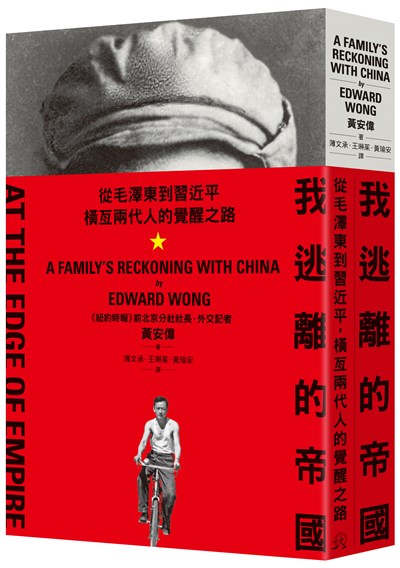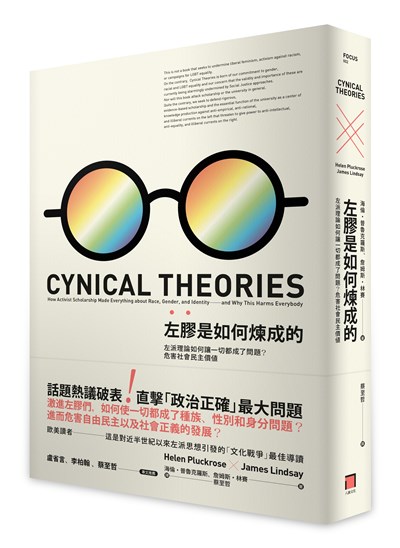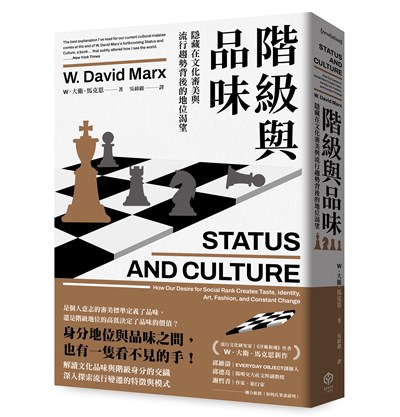中華民國建國到明年將達100週年,全球公認民主政治在中華民國台灣算是有點成就,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從歷史學者的角度,為他自己即將80歲,也為民國將達100年,作了一些反思並集結成書。他指出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至今,最欠缺的仍是人文素養,使民主政治的操作顯得較粗糙,也欠缺深刻的反省。
在這本《人文與民主》新書中,余英時反覆討論民主與人文的關係,強調這不應只是一種制度,而應該是一種生活方式與生活態度;民主還是須要文化作支撐,包括選舉一人一票等值、政黨輪替等,在台灣都已經被大家接受。但是,台灣社會的人文精緻度還不夠,大家還有努力的空間。
余英時也討論到民主文化的重建、民主文化與菁英文化的關係、台灣的人文研究展望、科學與人文的研究為什麼必須均衡發展。正是因為常常有感而發,使他在各種演講場合反覆的談,強調台灣欠缺人文基礎,使台灣的民主成為民粹,而難達到民主更高的層次,這次將演講稿彙整成書,希望在國人以台灣的民主成果為傲時,提醒大家還是要做深刻的反省。
文章節錄
臺灣未來人文研究之二:找自己的文化傳統,不隨西學起舞
王國維有兩句詩:「人生過後唯存悔,知識增時轉益疑。」我們可以用來代表他對求知的基本態度。扼要地說,這便是一種開放的態度。一個人的知識不斷去增加,因此必須隨時修正自己前面所得到的論斷,梁啟超也宣稱,他在知識上不惜以今日之我來批評昨日之我。他不贊成他的老師康有為的「太有成見」,三十歲以後便死守早年的學說,一字不肯改變。這一開放的心態,早在宋、明時期便已發展得很普遍了。明末顧憲成論朱熹和陸象山的不同,提出朱常常覺得自己在認知上可能有錯誤,陸象山則常常自以為是,不承認有任何錯誤的可能。顧氏分別稱之為「有我」與「無我」。即是說,朱熹已擺脫了孔子所反對的「我執」,而象山則未免尚有「我執」。我覺得中國傳統學者這種開放態度和西方哲人大致是相通的。姑舉卡爾.波柏(Karl Popper, 一九○二~一九九四年)為例,他強調知識並無止境,我們永遠不斷在嘗試與錯誤之中向前摸索。如果理論與經驗不合,我們只能尊重客觀經驗,修改或放棄錯誤的理論。能夠證明為錯誤的才是知識的對象。他以「證誤」(falsification)原則取代邏輯實證論者的「證實」(verification)原則,道理便在這裡。因此波柏將科學與宗教及形而上學嚴格地區別開來,後二者追求的是永恆不變的「真理」,也沒有任何「經驗」可以修正宗教的信仰或形而上的論斷(也就是不可能「證誤」的)。波柏所說的知識雖以自然科學為主,但也包括社會科學和史學。我們所談的人文研究,既是「研究」,當然也和「科學知識」同一性質,最多不過精確的程度不同而已。
我在上面特別講了求知態度的問題。為什麼呢?因為我想對人文研究的未來提出一點個人的意見。大概自二十世紀初年開始,中國便有不少為西方理論所折服的知識人,所以《國粹學報》(一九○五~一九一一年)已諷刺「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的風氣。大概因為震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緣故,清末知識人對於十九世紀西方的社會進化說──如孔德(Auguste Comte, 一七九八~一八五七年)和史賓賽(Herbert Spencer, 一八二○~一九○三年)──都幾乎抱著一種盲目信仰的態度。他們認為西方社會學家已發現人群進化的普遍規律,中國歷史進展的階段也逃不出這一普遍規律的籠罩。崇拜西方理論的心理早始於清代末葉,這是最明白的證據。但是這一心理在「五四」以後越來越深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歷史階段論竟能在中國稱霸數十年,至今仍無人敢公開挑戰,除了政治原因之外,也不能不歸咎於這一心理根源。臺灣人文學界對西方社會科學、哲學、文學、歷史種種新理論也往往趨之若鶩。大概於一九七○年代起,臺灣人文研究方面的青年學人已明顯地表現出這一傾向。我記得七○年代末嚴耕望先生到耶魯訪問半年,他曾一再和我談到西方理論為什麼會被新一代的中國治史者奉為金科玉律?可見他深為當時的學弊所困惑,中國文、史、哲研究之所以遲至今日尚未能自成格局,恐怕和崇拜西方理論有關。在有意無意之間我們已把西方文化看作標準的範式,凡是西方見長而中國相形見絀的部分,我們都說這是因為中國「落後」的緣故。例如中國沒有西方式的「資本主義」,也沒有西方式的「科學」,一般的看法認定這是西方跑在前面,我們尚未追上。這種說法首先假定歷史進程具有普遍性,中國和西方都依照同一模式和階段前進。我們似乎沒有考慮到:也許中國與西方各自走了一條獨特的道路,根本談不上誰「先進」誰「落後」的問題。
事實上,無論是史賓賽或馬克思都是根據西方的歷史經驗來建立他們的社會演進的理論的;他們並沒有說此理論可以普遍應用於一切文化與社會。馬克思甚至堅決否定他對西歐歷史的理論觀察可以用之於俄國。今天的情況當然已完全變了,無論是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似乎再也不說我們已發現了人群演化的普遍的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行之百世而不惑」。與此同時,西方人文社會學者現在也十分自覺地要跳出「西方中心論」的陷阱,不再將西方歷史進展的模式加強於非西方社會、文化之上。這是一個新的起點,我們可以直接面對中國資料所透顯的歷史內部脈絡,去試著重建中國文化的獨特形態及其成長歷程,而不必把中國史研究勉強納入西方任何整齊的公式之中。必須聲明,我並不是反對「理論」,更不是強調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認為它完全不能接受西方理論與方法的處理。相反的,我很尊重西方第一流學人關於人文、社會、歷史現象所提出的許多啟發性的假說(即理論),也欣賞他們常常發展出新方法、新觀點,足以開拓人文研究的視野。我僅僅堅持一點,一切已普遍流行的理論或假說,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經驗事實上面,因此其有效性終究是有限度的,不能視為「天經地義」,而且再高明的理論,只要與經驗事實相違背,便不能不作修正。
展望臺灣的未來,中國文、史、哲的研究應該是新一代中國學人的重點。中國人研究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總是占有一定的優勢。如果我們不再為西方既有的理論所震懾,又能拋棄以西方文化為普遍模式的偏見,我相信不出二、三十年臺灣便有可能成為中國人文研究的中心之一。研究中國文、史、哲的人不會太多,也不需太多。關鍵在於培養高質量的少數人才,富於獨立的判斷力,不致因西方風吹草動便跟著腳步虛浮起萊,那麼一個堅實的人文研究的傳統便會慢慢形成了。
附記:這是我今年(二○○八)六月二十八日在國立政治大學的一次談話。題目是政大方面建議的。我當時沒有時間預先寫出講稿,只好即席發言,因此講詞不免鬆懈,這次讀到整理出來的記錄之後,我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和重寫,思想脈絡仍舊,但表達和實例方面變動較多。
(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余英時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