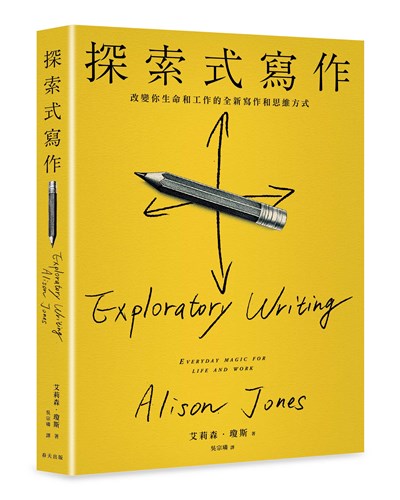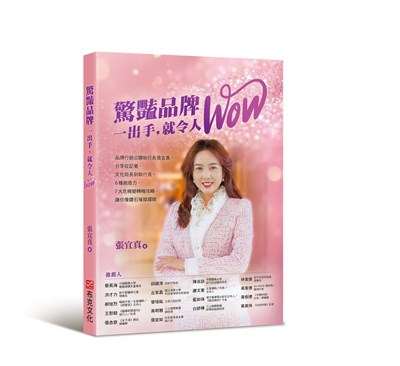本書跟隨著元代帖木兒派員親往真臘(柬埔寨)觀察研究寫成13世紀柬埔寨史最重要著作《真臘風土記》的歷史文化刻痕,經由作者美學觀點,產出獨特的人文觀察與省思,令讀者領略到吳哥的旅遊風情,也可深一步地看出吳哥之旅的人文深度和歷史魅力,與一般的旅遊筆記實在大不相同。
文章節錄
《吳哥之美》
美,總是走向廢墟
吳哥王朝留下了一片遼闊的廢墟。
在廢墟間行走,有時候恍惚間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時何地。
寺廟多到看不完,法國人編的旅遊書把行程規劃成三天、四天、五天、七天、九天……不等的內容。
最短的行程一定是以吳哥寺和巴揚寺為重點,找到了吳哥王朝文明繁華的巔峰,找到了城市布局的中心,再慢慢從中心向四周擴大,依據自己可以停留的時間規劃出希望到達的範圍。
Ming,我在廢墟間行走,我不知道自己如此短暫的生命是否可以通過、經驗、體會上千年繁華剎那間成為廢墟的意義?
有時候我依靠著一堵傾頹的廢牆睡著了。我想停止行走,停止下來,沒有繼續接下來的行程,沒有此後的規劃,我想靜靜在睡夢的世界,經驗時間的停止。我想覺悟:自己的短暫生命,城市繁華,帝國永恆,都只是睡夢裡一個不真實的幻象而已。
吳哥的建築美嗎?吳哥的雕刻美嗎?
為什麼一直到此刻,使我錯愕悸動的,其實是那一片片的廢墟?那些被大樹的根擠壓糾纏的石塊,那些爬滿藤蔓苔蘚蛛網的雕像,那些在風雨裡支離破碎的殘磚斷瓦,那些色彩斑剝褪逝後繁華的蒼涼,那些原來巨大雄偉、卻在歲月中逐漸風化成齏粉的城垣宮殿,一個帝國的永恆,也只是我靠在傾頹的牆邊,匆匆片刻睡眠裡一個若有若無的夢境吧!
許多朋友詢問:去吳哥要多少天?
如果還在夢境的廢墟牆邊,我必定難以回答這個問題吧!
如果不是膚淺的觀光,不只是在吳哥,走到世界任何一片曾經繁華過的廢墟,我們都似乎是再一次重新經歷了自己好幾世幾劫的一切吧?自己的愛,自己的恨,自己的眷戀,自己的不捨,自己的狂喜與沮喪,自己對繁華永恆永不停止的狂熱,以及繁華過後那麼致死的寂寞與荒涼。
我在廢墟中行走,我不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
我穿過一道走廊,方整的石柱約兩公尺高,柱頭四周雕刻了一朵朵蓮花。蓮花輕盈,承接著上面粗壯沉重的石樑。石柱四面刻了非常精細的浮雕,像最精緻的刺繡,繁複綿密。浮雕刻得很淺,好像皮影戲映照在潔淨白布上的幻影,華麗迷離卻又完全不真實。石樑上的雕刻比較深,樑的上下緣也都裝飾了蓮花。蓮花之上,一尊尊的神佛端坐沉思冥想。
大部分的佛像已經被盜,從石樑上整尊被砍挖下來,原來佛端坐的位置,只剩下一個使人冥想的空洞。
Ming,我面對的是一個冥想的空洞,那精細雕鑿的神龕裡一個消失的人形。祂仍然端坐著,祂仍然陷入沉思,祂還在冥想,而祂的肉身已消逝得無蹤無影。
我想到「佛」這個字,從梵文翻譯而來,採取了「人」與「弗」的並置。「弗」是「沒有」,「弗」是存在的消失;那麼,「佛」也就是「人」在消失裡的領悟嗎?
廊是一個通道,原來上面有覆蓋的石板屋頂。屋頂坍塌了,大片的石板摔落在地上,阻礙了通道。
廊的盡頭是一道門,長方形的門,用重複細線凹槽的門框裝飾,好像要加重強調「門」的意義。
我穿過廊道,看到柱子,看到橫樑,看到屋頂,看到人在空間裡完成的建築。看到雕刻,看到花紋與蓮花裝飾,看到已經消失的佛像。
我穿過廊道,穿過我自己的生命,看到成,住,壞,空;看到存在,也看到消失。
我停在長方形的門前,門前有兩層台階,門被放置在比較高的位置。因為年代久遠,門框有點鬆動了,原來密合的地方露出一、兩指寬的縫隙。門兩側侍立的女子,手持鮮花,衣裙擺盪,應該是婀娜多姿的嫵媚,卻因為整個建築的崩毀肢解,女子的身體也從中央分開,分解成好幾塊。
這是再也拼合不起來的身體,好像身體的一部分在尋找另外一部分。頭部大多不見了,留下一個茫然不知何去何從的身體。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停留在門前。這扇門像一個神秘的界限,界限了室內和室外,界限了這裡和那裡,界限了執著和了悟,界限了生和死,界限了此生和來世,界限了有和無,界限了進入和離去,界限了抵達和告別……
這裡幾乎是遊客不會到的地方,這裡被崩塌的石塊堆疊阻礙,不容易行走。大樹的根四處生長蔓延,屋頂上垂掛下來頑強的薜荔藤蘿,一些寄宿的野貓被驚嚇,唿的一聲,從陰暗的角落竄出,慌亂奔逃而去,留下死一般的寂靜。
留下我一個人,聽著自己從前世一步一步走回來的腳步聲,知道這一片廢墟等待我許久許久,等待我穿過這段走廊,等待我站在這長方形的門前,等待我隔著一千年再來與自己相認。
或許,吳哥窟真正使我領悟的是時間的力量吧!
一位當代的錄影藝術家維歐拉(Bill Viola),用攝影機記錄物質的消失。經過剪接的節奏,維歐拉使觀者感受到時間,感受到時間在物質上一點一點消失的錯愕。一條魚,存在著,像十七世紀荷蘭畫派用最精細技法畫出來的魚,每一片魚鱗的反光,魚的眼睛在死亡前呆滯茫然的瞪視,存在這麼真實。然而,維歐拉記錄了真實在時間裡的變化。他使我們看到魚的腐爛,蒼蠅嗡嗡飛來,密聚在魚的屍身上,螞蟻鑽動著,他剪接的節奏使時間的變化可以用視覺觀察,魚肉不見了,剩下一排像梳子一樣的魚骨,剩下魚頭,剩下瞪視的眼睛和尖利的牙齒。
歐洲人在十九世紀最強盛的時候走進了吳哥,他們讚歎吳哥文明,讚歎建築之美,讚歎雕刻之美,他們從牆上砍挖偷盜精美的神佛,甚至把整座石雕橋樑拆卸帶走,巴黎的居美(Guimet)美術館至今陳列著從吳哥盜去的文物。
吳哥其實早已是一片廢墟。五百年前吳哥就被毀滅,城市被火焚,建築上的黃金雕飾和珠寶被劫掠,人民被屠殺,屍體堆積如山,無人收埋,致死的傳染病快速蔓延,最後連侵略者也不敢停留,匆匆棄城而去。吳哥被遺忘了,熱帶大雨沖去了血跡,風吹散了屍體腐爛的臭味,白骨被沙塵掩蓋,血肉肥沃了大地,草生長起來,大樹扶疏婆娑,有人回來,看到一片廢墟,若有所思。
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強盛的巔峰走進了吳哥廢墟,他們震驚古文明的偉大,他們想佔有美,他們用最貪婪粗暴的方法掠奪美、霸佔美,試圖把美佔為己有。
但是,美從不屬於任何私人。
美無法掠奪,美無法霸佔,美只是愈來愈淡的夕陽餘光裡一片歷史的廢墟。帝國和我們自己,有一天都一樣要成為廢墟;吳哥使每一個人走到廢墟的現場,看到了存在的荒謬,或許慘然一笑。
斤斤計較藝術種種,其實看不到真正動人心魄的美。
美,總是走向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