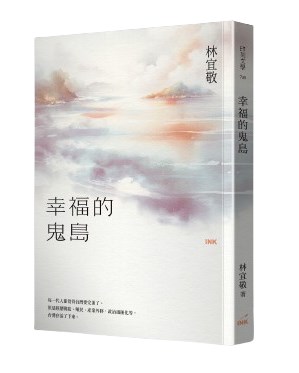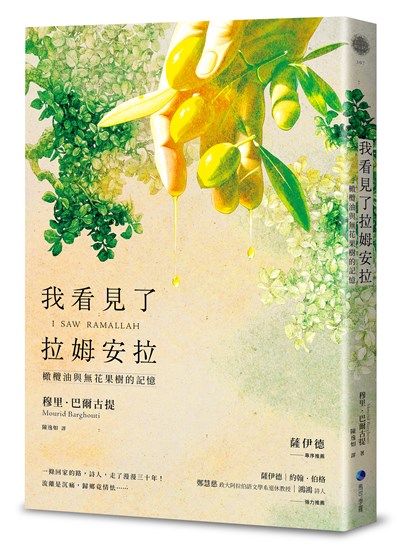
1967年,以色列占領了加薩與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從此流離失所。當時正在埃及念書的巴勒斯坦詩人穆里・巴爾古提也再沒回到巴勒斯坦。在外流亡三十年後,1996年,他終能回返家鄉。幾百年來,橄欖油對巴勒斯坦人來說一直是禮物、是珍藏、是家族的財富。然而,當巴爾古提再回到巴勒斯坦,這裡再也產不出橄欖油,院子裡的無花果樹也早被砍去。這段流亡與回家的心路歷程,在以巴衝突仍未結束之時,繼續傳達著。
內容節錄
《我看見了拉姆安拉:橄欖油與無花果樹的記憶》
我站在這片國土的塵土之上,這片國土的土地上。
我的國家負載著我。
此時此刻巴勒斯坦不是流亡女性頸子上用金鍊子鍊著的金地圖。每次看到那些圍繞她們頸間的地圖,我經常在想,加拿大女人、挪威人或中國人是不是也像我們的女人在脖子上戴著地圖。
我有一次對朋友說:「當巴勒斯坦不再是晚禮服上搭配的鍊子,不再是飾品、記憶或金色古蘭經,當我們可以走在巴勒斯坦的土壤上,可以拍掉領口和鞋上的塵土,匆匆忙忙地趕著去做一些生活瑣事,那些平凡無奇又無聊的事,當我們對著巴勒斯坦的熱天氣發牢騷,覺得待在那裡生活太久而發悶,那就真的和它非常親近了。」
現在它就在你面前,你正要展開旅程。好好看它一眼。
大樓的對面我碰到了第一個巴勒斯坦人,他執掌的事很清楚明白:這位有了年紀的瘦削男人在牆邊陰影處擱了一張小桌子,坐在桌前,在涼蔭中躲避六月的燠熱。他大聲叫住我:「來這邊,兄弟!買張車票吧。」
再也沒有比被人這樣稱呼而更感寂寞的事。「兄弟」這個關鍵詞扼殺了兄弟之情。我望了他半晌。
我用約旦錢買了票,往旁邊走開兩三步,然後停住,然後往他的方向跑去追巴士。不。我其實並沒有跑,我完全就像平常那樣走著。我內心深處有什麼東西正跑著,我坐在巴士裡面,等到車裡漸漸坐滿像我一樣過了橋的人。我問司機我們要去哪裡。
「到杰里科之家(Jericho resthouse)。」
我終於進入了巴勒斯坦。但是這些以色列國旗是怎麼回事呢?
我從巴士窗口向外望,看到他們的國旗在一個又一個檢查崗哨出現又消失,每隔幾公尺國旗就出現一次。
有一種我不想承認的沮喪感覺,一種不能成就的安全感。
我的眼睛沒有離開車窗,過去那些已經過去了的畫面一直留在眼底。
在這輛緩慢的巴士上,我回想起,好像不過是昨日的事,當時在卡拉凡飯店早餐室,我們家人在一九六七年之後的首次聚會。
那是戰後的夏天,一九六八年夏天。我在科威特工作,我母親還有最小的弟弟阿拉都在拉姆安拉,我父親在安曼,馬吉得當時在約旦大學,慕尼夫則在卡達工作。
透過各種可能的聯絡管道,我們決議在安曼會面。我們陸陸續續抵達吉伯爾盧韋伯達(Jebel al-Luwaybda)的卡拉凡飯店,這家小規模的精緻飯店有三、四層樓高。
自從戰爭把我們拆散之後,這是我第一次和父母兄弟見面。我們訂了三間相連的房間。飯店本是供睡眠之用,我們卻睡不著。早晨來臨的時候,我們都吃了一驚,好像它背離了太陽系的運作,好像它的作息已經不符合邏輯,在意料之外。
我這輩子沒有嚐過任何如同那個夏日的早餐。
經過詭譎的數個月之後,能夠和全家人一起開始新的一天是美好的。我們會互相注視著對方,好像當下大家都是第一次發現對方的存在,每天我們都重新溫習母愛、父愛、兄弟之情與身為人子的感覺。奇怪的是我們都沒有把那種感覺說出來,能夠聚首飯店內的喜悅飄蕩在空氣中,圍繞著,我們感受著,卻又不想讓它太招搖,彷彿那是個祕密,彷彿我們都被要求不能張揚。
飯店本身,還有飯店的概念就已經確定了短暫的聚首、交會和結束。從第一個晚上起,我們的聚首就變成了必然要離別的恐慌。緊張的氣氛交雜著快樂。我們在決定沙拉是不是要加橄欖油的時候意見分歧,有的人想要切成小塊的沙拉,有的人想要大片的沙拉。
就在我們決定是不是要稍微出門走走的時候,緊張局勢攀升到了最高點:有人建議去造訪住在安曼的親戚,有的人根本不想出門,還有人建議去別處。但是這過程總是笑笑鬧鬧,雖然內容記不太清楚了,我卻還清楚記得那氣氛。
在卡拉凡飯店,我又重新認識了我的兄弟和父母。對每個人而言,總有些我不完全知道的新特殊狀況。
自從一九六七年開始,我們的所作所為都是暫時的,而且要等局勢明朗再說的事,可是事情過了三十年還是未見明朗。就算現在所做的事對我而言也是不清不楚的。我總是憑著一股衝動做事,也不多做他想。也許想太多就不能稱之為衝動了吧?
一九四八年戰亂中,難民都出於「暫時」的考量,到鄰國尋求庇護。他們任爐火上的東西煮著,以為自己幾個鐘頭就可以回來了。他們「暫時」四處待在難民營與鐵皮屋,突擊隊全副武裝,「暫時」從安曼開戰,「暫時」打到貝魯特,然後又「暫時」移師到突尼斯和大馬士革。我們「暫時」為解放草擬了臨時綱領,然後他們說「暫時」接受了奧斯陸和平協議,諸如此類。每個人都對自己和別人說:「就等情勢明朗。」